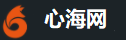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是:心海E站 > 文案短句 > >正文
王夫之(王夫之的儿子?)
发布时间:2023-12-04 10:24:12 admin 阅读:59
王夫之的儿子?
王夫之至少有四子,比较有名的是次子王攽与四子王敔。
王攽,字曷功,是王夫之前妻陶夫人生的。他出生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当他二岁时,母亲陶夫人就逝世了。王攽的妻子是衡阳刘近鲁之女。刘家在小云山下,家有藏书楼,藏书数千卷。王夫之常到刘家看书,既是好友,又是儿女亲家,彼此的友谊是很深的。王攽卒于何年,文字缺少记载。他著有《诗经释略》,但也未见刊。
王敔(1656年-1731年),字虎止,是王夫之的第二任妻子郑氏所生,为王夫之的第四子。入邑庠,为诸生,娶刘象贤之女,生一子王范,还有二女,曾修《湘乡县志》。癸未年(1703年),湖广学政潘宗洛请王敔刊刻船山遗书。著有《蕉畦存稿》《笈云草》《姜斋公行述》等。
王夫之对传统中医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船山国学日报20181130】
王夫之对传统中医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文/徐仪明
王夫之认为"大黄、黄芩、黄连、黄栀、黄柏之类"药物是火热之物而非寒凉之剂。这样的说法是否具有理论依据且其理论依据何在?从中药学史来看,自《神农本草经》到李时珍《本草纲目》,都认为大黄,黄连,黄柏,黄芩之类药物其性味为苦,为寒,为凉,其功用为清火逐水祛湿泄利解毒,藉此可使患者的实热之证而得到消解。其理论依据即五行生克制化理论中的以水克火。然而,王夫之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五行之化,唯火为速",因此大黄,黄连类药物之所以能够迅速清除肠胃积聚,散瘀止疼,其原因并非是以寒制热,以水制火。恰恰相反,是以热祛热,以火制火.王夫之说:"火挟火以速去,则府藏之间,有余者清以适,不足者枵以寒,遂因而谓之寒,不可谓其性寒也。呜呼!不知性者不以用为性,鲜矣。天地之命人物也,有性有材有用;或顺而致,或逆而成,或曲而就,牛之任耕,马之任乘,材也。地黄、巴戟天之补,栀,檗,芩,连之泻,用也。牛不以不任耕、马不以不任乘而失其心理之安。地黄、巴戟天之黑而润,受之以水;栀,檗,芩,连之赤而燥,受之于火。乃胥谓其性固然,岂知性者哉!"为了说明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唯有火的性质是往来疾忽,变化迅速,泻火,化火,清火,败火者只能是火。王夫之提出了"性""材""用"三个概念。栀、檗,芩、连等攻下之药,经过炮制以后,其色深黄且泛红而干燥;地黄,巴戟天等滋补药物经过炮制以后,颜色乌黑而润泽。前者属火而性燥,后者属水而性寒,这就是药物的"性"。而像牛能耕地,马能骑乘,药物能够治病一样,这些属于事物的"材"。至于自古以来本草类书上所记载的大黄,黄连等药物其性质属于寒凉的说法,王夫之认为这是不懂得什么是“性"、什么是"用",而将两者相互混淆了。"泻下"或"寒凉"只是大黄,黄连等的"用",即作用,而不是它们的属性。显然,王夫之对温热之病的治疗颇有心得。他认为肠胃实热之郁火,必须以火引之而去。他说:"药食不终留于人之府藏,化迟则益,化速则损。火郁而有余者不消,则需损耳。损者,非徒其自化之速不能致养,抑引所与为类者而俱速。”船山神契于仓公"火齐"之术,以大黄等"火性"药物消损脏腑中"火郁而有余者"。因其能够"以火引火速去",所以效若桴鼓,立竿见影。在我看来,王夫之把自古以来本草书上所说的这些个寒凉药物的性质视为火热,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其实这里存在着很深刻的医学学术背景和哲学思想背景。
本期编辑:井泉
主办单位:船山总会
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纪念倒计时:还剩313天
王夫之的循天下之公什么意思?
“循天下之公”意思是遵循天下的公理。出自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原文: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
扩展资料: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中国复兴的大道。
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30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迭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
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
王夫之壮年时,明清两朝交替,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经受过坎坷的政治流亡生活的考验和锻炼,同时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使他的进步思想趋于成熟。迫于抗清形势逆转,王夫之遁迹林泉,近四十幽居穷乡僻壤,荒山野岭,苦其心志,联系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找挽救危局的革新之路。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请参考!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哪个朝代的人明末清初
哲学成就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文学成就
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史学成就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王夫之作诗怀念亡妻,诗中无一字直接写悲,却句句悲哀令人动情
悼亡是诗词中很常见的题材,相信大家也读过不少悼亡名篇,譬如:《诗经·邶风·绿衣》、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元稹的《遣悲怀》、苏轼的《江城子》、贺铸的《鹧鸪天》、陆游的《沈园二首》、纳兰容若的《南乡子》与《金缕曲》,今天咱们来读一读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妻子死后写下的《悼亡四首》中的一首。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为学者王朝聘。王夫之蒙学很早,3岁就跟着哥哥学习识字,13岁中秀才,23岁中举。崇祯皇帝死后,他一直希望能够恢复明朝天下,于是在衡山脚下举兵阻止清军南下,失败后投靠南明,辗转多地,后见复国无望,隐居深山,誓不剃发,直到康熙年间去世。
王夫之一生虽有三个妻子,但是对第二任妻子郑氏用情极深。顺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
两人在一起的十年间,王夫之可以说是不断地流亡,郑氏跟着他吃尽苦头,最惨的时候,几天没有饭吃,直到后来王夫之选择隐居,日子才稍稍安定。两人在一起度过了艰难时刻,哪怕是郑氏已经去世,哪怕他枕边有了新妇,但是他仍旧会时不时想起郑氏,想起那些年两人的日子,每一年郑氏祭日来临,王夫之的心情都会特别低落。
在民间,有十年大祭的习俗,那年,王夫之妻子郑氏去世十年,王夫之积极准备郑氏的祭奠仪式,同时也想把胸中积郁多年的思念进行宣泄。他借组诗《悼亡四首》回忆郑氏与自己一起度过的日子,回忆郑氏与自己的永诀,今天咱们就来读一读其中一首:
十年前此晓霜天,惊破晨钟梦亦仙。一断藕丝无续处,寒风落叶洒新阡。
这首诗一开始,王夫之就用了七个字来回忆与郑氏诀别那日的悲凉的场景,“十年前此晓霜天”,十年前的今天,那是一个下了一宿寒霜的清晨,眼看着妻子卧病这么久还没有好转的迹象,自己内心比外面的寒霜还要冰冷。
突然,妻子咽气了,这太让王夫之意外了,明明早晨是一天的开始,而晨钟敲响之时,却是妻子仙游之刻,“惊破晨钟梦亦仙”。“惊破”二字足见王夫之对妻子的去世毫无准备,让他受惊极大。
人生不能复生,从此深爱夫妻阴阳两隔,就要那折断的藕虽有丝相连,终究不能完好如初,妻子去世,王夫之思念不已,两人终无再相逢之时,“一断藕丝无续处”,王夫之内心已然是悲伤到极致。
妻子亡故之后,王夫之将其安葬,并修了墓道,方便自己前往祭祀,这十年祭祀之期,但见墓道之上,寒风将树叶带落下来,铺满地上,“寒风落叶洒新阡”。以景衬情,足见王夫之内心的凄凉与孤寂。
妻子去世十年,如此漫长的岁月,王夫之依旧对郑氏念念不忘,足见两人感情深厚,也更加可见他内心的孤单与寂寞。
解读:王夫之的气论与他的生死观
梁绍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湖南长沙410003)
在我国古典哲学的范畴中,人们对气的认识往往是和生与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观念的起源和兴盛又最早形成于我国第一个哲学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易传》时代。
《易传·系辞》在追溯易的起源的同时追溯物种的起源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我们知道,物种的起源必须有雌雄两性,这就是所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有雌雄两性就得有乾坤两道,这样,人的起源与易理的起源也就同步进行了。那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具体物质又是什么呢?《系辞》在另一处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原来构物的材料是精气,也就是充斥于宇宙之间的气。气聚而为物,散而为气,所谓游魂,也就是游散之气。气的聚散就是物的存没,对人来说,也就是生死,所以《系辞》又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人的生命推其原始是什么呢?是气。反其终极又是什么呢?仍然是气。躯体血肉,不过是气的一时凝聚罢了。气聚而生,气散而死,这就是人的生命的全过程;懂得了这个道理,才算从根本上懂得了什么叫生,什么叫死。这就是“故知死生之说”的学问。
对于《易传》的这个思想,尽管代代相传,而且被儒家奉为经典,但从思想上认同的并不多,直至北宋时代的思想家周敦颐、张载,才真正接受并弘扬了《易传》的思想。张载在《正蒙》一书中构建了他彻底的气一元论,而周敦颐更是把宇宙的本原推到了气前的“无极”阶段,以至与当代宇宙学说的理论相对应。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著《张子正蒙注》,他虽然在宇宙本原的问题上从周子的“无极”退到了“太极”,但在将张载的气一元论发挥得漓淋尽致的同时,对人的死生作了可贵的探讨。
一 王夫之的气一元论
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能见的自然物体和不能见的茫茫空间又都是些什么呢?王夫之认为,都是气。气是宇宙的本原,气是制造万物的材料。看得见的是气的凝聚,看不见的是气的消散。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气,看得见的是有形的气。气是它的本体,物是它的客形。他解释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一语说:“于太虚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气自足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日月之发敛,四时之推迁,百物之生死,与风雨露雷乘时而兴,乘时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来谓之客。”(《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认为,宇宙在没有成形有形物质之前,全是它原本存在的气。因为聚散变化,出现了各种有形的物质,但仍然是这些气,既不减少,也不增多。因气的聚散变化的物质有哪些呢?王夫之认为,包括太阳月亮的出现,春夏秋冬的推迁,百物的生死,以及风雨露雷,它们都是“乘时而息”的“客形”。客形,从字面上说,也就是作客的形体。这是将社会现象运用于自然现象的比喻。在社会现象中,任何客人都是外来的,而且都是要走的,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说“有去有来谓之客”。“客形”,生动深刻地概括了这一特定现象的时空规定性。与之相类似,宇宙间任何有形之物,都是“客”,都是有来有往,有聚有散。大至日月星辰,四时寒暑,小至百物生死,以及自然现象的风雨露雷,都只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现象,因时而来,因时而去。来则为聚,去则为散。聚时为有形之物,去时为无形之气。尽管现象不同,但其理则一。当然,虽说都是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现象,但时间的长短和空间的宽窄却大不一样。比如风雨露雷,占的空间虽然比较大,但时间却是短暂的,所谓骤雨不终朝,飚风不终夕,它与太阳、月亮,不能同日而语。至于“百物生死”,更是千差万别。百物中有朝生夕死的,有一岁荣枯的,更有数十年数百年一死生的。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乘时而息”,都是个时间与空间的概念。
这里,王夫之有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他把有生命的“百物生死”和风雨露雷的自然现象,乃至从来被人视为永恒不变的日月,统统看成是同一性质的气的聚散现象。这个思想,因为用的是“发敛”一词,所以有不同的理解。他的儿子王敔在句末加注说:“发敛,谓日月出入之道。”出入之道指的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出没现象,这与气的聚散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王夫之的思想里,“发敛”就是聚散,“发”有发生之意,就由气到形而言;“敛”有收敛之意,就由形到气而言。他在注张载“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一语时发挥说:“日月、雷风、水火、山泽,固神化之所为,而亦气聚之客形,或久或暂,皆已用之馀也。”当然,日月、水火、山泽是如何形成的,十分玄妙,故谓之“神化”,但王夫之却大胆地肯定它们都是“气聚之客形”,所不同的仅是时间上“或久或暂”的区别。这就是说太阳、月亮、山泽,尽管存在的时间极久,但仍然是气聚的客形,有一天终究要返回太虚而成为气。这样,王夫之的气一元论,也就达到十分彻底的程度了。
二 王夫之的大轮回思想
王夫之虽然大胆肯定任何有形的物都是由无形的气转化而来的,但无形的气如何转化为有形的物,有形的物又如何返回为无形的气,除了“神化”一语而外,似乎没有说出更多的道理(事实上也说不出道理)。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王夫之既反对有宇宙的大轮回,也反对有人生的小轮回。他在概括张载《张子正蒙·太和篇》第一大段的要旨说:“此章乃一篇之大指,贞生死以尽人道,乃张子之绝学,发前圣之蕴,以辟佛老而正人心者也。朱子以其言既聚而散,散而复聚,讥其为大轮回,而愚以为朱子之说正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
王夫之没有正面批判佛老,而是直接驳斥朱熹的大轮回说。原来朱熹曾经和他的学生讨论张载的《正蒙》一书,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正蒙》说道体处,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说气。说聚散处,其流乃是个大轮回。盖其思虑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语道理,惟是周子说‘无极而太极’最好”。(《朱子语类》中华书局本第七册第2533页)又说:“横渠辟释氏轮回之说,然其说聚散屈伸处,其弊却是大轮回。盖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同书2537页)朱熹是理一元论者,所以批评张载只说气而不说理,认为他的聚散没有从“性分”上说,而是直接从气的转化现象推理出来的,最后似必形成宇宙的大轮回。并且还直接与佛家的观点作对比,认为佛家的思想是作为个体一个一个地各自轮回,而张载的思想是将宇宙整个地作一次大轮回。对于朱熹的这些讥评,王夫之的反驳可说是苍白无力。首先,在立论上不仅是无力的,而且是紊乱的:“愚以为朱子之说正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朱子说了什么呢?朱子说的是张子的思想是大轮回,说朱子之说近于释氏,不正好说明张子的思想近于释氏吗?既然朱子之说就是张子的思想,那么驳斥朱子之说不正好在驳斥张子的思想吗?这究竟是帮了张子,还是帮了朱子?
最后,王夫之甩开了经典,引了许多通过自己观察所得的实例。他说:“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为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这就进一步说明,不仅人的生死是轮回的,连木、水、土之类的无生命物质同样是轮回的,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朱子之讥”的合理和公正。那么,王夫之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为他人说话而与自己过不去的文字呢?揣摩他的用意,可能是要用张载的气一元论来反对朱熹的理一元论,只是在立论和表述上出了毛病。实事求是地说,张载和王夫之关于气的聚散思想,本身就是大轮回理论,只是王夫之不敢承认罢了。其实宇宙本身是循环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就是德莱柏的反对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生物的生命的时间,正如生命和自我意识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狭小短促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循环,实际上就是被朱子所讥的张载、王夫之主张的大轮回,只是说得更加具体,更加具有鲜明辩证思想和科学性。恩格斯首先肯定物质运动是“一个永恒的循环”,是“无限时间内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只是这个循环的周期是十分漫长的,漫长得连地球存在的年代都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来计算。这样,不仅不存在释氏的“个个各自轮回”,恐怕也不是朱熹指出的“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了。由此可见,朱熹的讥评是一针见血的,王夫之的辩白是多馀的,而早于恩格斯818年的张载有与恩格斯相似的宇宙观,是十分可贵的,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
三 王夫之的生死观
王夫之虽然秉承张载“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的思想,认为物都是气的凝聚,但是,不同的物又是由不同的气按不同的程序构成的。他说:“聚则见有,散则见无;既聚而成形象,则才质性情各依其类。同者取之,异者攻之,故庶物繁兴,各成品汇;乃其品汇之成,各有条理,故露雷霜雪各以其时,动植飞潜各以其族,必无长夏霜雪、严冬露雷、人禽草木互相淆杂之理。故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治气恒于治,乱气恒于乱,屈伸往来,顺其故而不妄。不妄者,气之清通,天之诚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在这里举出了各种不同因气聚而成形的物:动植飞潜,人禽草木,以及霜雪露雷等等。既然同是气的聚散,为什么会有动植飞潜、人禽草木的区别呢?这是由于不同的气按照不同的条理、时值依类成形的。比如人,人是怎样成为人的呢?“人者动物,得天之最秀者也,其体愈灵,其用愈广。”(《张子正蒙注·动物篇》)所谓“最秀”,说的是气的最秀,最秀之气才能成为动物。但成为动物又不一定能成为人,要想成为人,还得有别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时位相得”。“时位相得则为人,为上知;不相得,则为禽兽,为下愚。”(《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什么叫“时位相得”呢?王夫之没有解释,无非是最秀的阴阳二气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特殊会合。其实这是蛋白体的组合问题,是最尖端的学科,以今日高度发达的科学尚且不得解其迷,自然不是三百年前的王夫之所能说得清楚了。
这里还有一个同样难以解释的问题:“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治气恒于治,乱气恒于乱。”据此说来,人之有善恶,社会之有治乱,不仅全是由气决定的,而且是不可更改的,因为恶气形成的人必然是恶人,乱气成形的社会必然是乱世。这样,不仅有把气的作用绝对化之嫌,似乎又与王夫之自己提倡的人生主旨相矛盾。他在注张载的“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一语时说:“气无可容吾作为,圣人所存者神尔。兼体,谓存顺没宁也。存者,不为物欲所迁,而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守之,使与太和絪缊之本体相合无间,则生以尽人道而无歉,死以返太虚而无累,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斯圣人之至德矣。”(同上)既然是“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那还有什么学聚、问辩、宽居、仁守之必要呢?
其实又不完全如此。王夫之在气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神”的概念,“气无可容吾作为,圣人所存者神尔”,(同上)气是无可作为的,能有所作为的,大概就在这“神”了。那么神又是什么呢?他在注张载的“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一句时说:“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气逐于物,役气而遗神。神为气使而迷其健顺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同上)原来作为气的起始阶段的太和,同时存在着两个东西,一是可象而无形的气,一是寓于象中的神。“神便是二气清通之理”,而理又是二气中阳健阴顺之性。人生守住了健顺之性,不因物感而气逐于物,不因逐物而役气遗神,就能“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则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全健顺之理以还造化,存顺而没宁”。(同上)
王夫之虽然将神解释为二气之理,健顺之德,似乎是一种纯自然现象,实际上讲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社会效应。他在另一处论神气关系时说:“神者气之灵,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则神犹是神也,聚而可见,散而不可见尔,其体岂有不顺而妄者乎!故尧舜之神,桀纣之气,存于絪缊之中,至今而不易。”(同上)神是不离乎气的,气散而归于太虚,神也同时归于太虚,所以尧舜之圣,桀纣之恶,其神其气,同时归于太虚的絪缊之中,永远无可改易。这里的“尧舜之神,桀纣之气”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无非在提醒人们,桀纣之恶和尧舜之圣一样,不仅永远存在于人间,而且永远存在于太虚,不可改易。
神气进入了太虚自然不能改易,但在未进太虚之前,也就是在生命存在之际,是否可以改易呢?王夫之紧接上文提出了一个完全与“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相反的命题:“然桀纣之所暴者气也,养之可使醇,持之可使正,澄之可使清也。其始得于天者,健顺之良能未尝损也,存乎其人而已。”根据这个思想,气又是可以培养的,其所以能够培养,是因为气在始得于天之时其“健顺之良能未尝损”。就是说,气虽然有善恶治乱之分,而且其性质无可改易,但随气而来的“神”是无区别的,都有阴阳之理,健顺之德。能不能以神役气,而不致以气役神,“存乎其人而已”。换句话,人的肉体需求的物欲无法改变,但精神是可以发扬的。人活着,追求的不是因气凝聚的肉体的满足,而是存乎气中的精神的发扬。“以人事言之,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所以事亲。存神以尽性,则与太虚通为一体,生不失其常,死可适得其体,斯尧舜周孔之所以万年,为圣人与天合德之极致。”(同上)故王夫之提倡的人生大旨,依然是修身成圣的思想,所不同的是把“形”(肉体)和“神”(精神)分作两事看。在他看来,两事都重要,但强调“心之神居形之间,惟存养其清通而不为物欲所塞”,最终达到“物我死生,旷然达一”的人生境界。
历代文人对王夫之的评价
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王夫之代表作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王夫之
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谭嗣同在《论六艺绝句》评价王夫之: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人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学者王朝聘的儿子。崇祯五年(1632年),考中秀才,组织“行社”、“匡社”。崇祯十五年,考中乡试。顺治初年,投靠永历帝朱由榔,参加反清斗争。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拒绝为吴三桂撰写劝进表。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湘西草堂,安葬衡阳县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1]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王夫之
王夫之主张废封建,其意不限于加强中央集权以确保国家一统,还着眼于“民力”的承受度,较具人民性.他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还着眼于倡导选举制,所谓“封建废而选举行”,布衣士子因此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其作为庶族士人反对封建贵胄特权的倾向.较之柳宗元以“势”论封建,王夫之则作了深度开拓:于“势”后探“理”.王氏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读通鉴论》卷一)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封建——郡县”之辩背后的历史规律性问题.在论及汉代抑制诸侯势力的举措时,王夫之说:“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天假之,人习之,浸衰浸微以尽泯.”(《读通鉴论》卷三)深刻说明主父偃单车赴齐而使齐国归服,并非主父偃个人力量所致,乃“天”藉其实现客观规律罢了.王夫之将秦废封建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说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名言.在这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颇相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在起作用,黑格尔归之于“绝对精神”,王夫之则归之为“理”,终之于“天”,从而把秦汉唐宋以来的“封建论”推到历史哲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