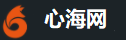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是:心海E站 > 文案短句 > >正文
巴金简介资料(巴金的《我的弟弟》)
发布时间:2023-11-28 13:01:30 admin 阅读:59
巴金的《我的弟弟》
★承继文匯传统 秉持讀書品质 ★文汇读书周报 ID: whdszb
《文汇读书周报》第1764号第三版“书人茶话”
(2019年5月27日发行)
王建军
“En La Malluma Nokto”和“Mia Frateto”,是巴金用世界语创作的两篇文学作品。前一篇是短剧,初刊1928年10月—12月《绿光》杂志第五卷第十—、十二期合刊,现存《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中译文存第十九卷“附录”;后一篇是小说,初刊1933年7月《绿光》杂志新一号,未存《巴金全集》,中译文为全集遗漏。
《绿光》是世界语杂志,1922年6月由上海世界语学会创办,巴金的挚友索非曾参与编辑。1928年12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后,由索非介绍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并曾负责编辑《绿光》杂志多期。
2014年《现代中文学刊》第五期刊发的李存光《1933年绥远归绥刊发的一篇巴金佚文——世界语散文〈我的小弟弟〉》(下文简称“李文”)一文,对巴金两篇世界语作品的翻译作了较详尽的介绍。文中说到:现存《巴金全集》的“En La Malluma Nokto”中 译 文《在黑暗中》,是他请北京师范大学周溪流翻译的;巴金自己的译文《在黑夜里》,则是他在1931年2月10日出版的《学生杂志》第十八卷第二号“学生世界语栏”找到的。“李文”还介绍,至今发现“En La Malluma Nokto”“已 有五种中文译文,译者分别为曾筠、小奇、巴金、周溪流、许善述”;“Mia Frateto”“则有两种中文译文,译者为杨令德、顾钟锦”。
“李文”说到的“Mia Frateto”两种中文译文,先见到的是顾钟锦的《我的弟弟》,载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我的小弟弟》是杨令德译的,发表于1933年9月3日《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Mia Frateto”的中译文“为全集遗漏”,应该是编辑《巴金全集》时,尚未见到或发现这两篇中译文的缘故。
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Mia Frateto”的中译文是否仅有以上两篇?2018年《点滴》第二期刊发的金传胜《巴金〈我的弟弟〉的中文本》(简称“金文”)竟然一下子刊布了三篇:署名“巴金”的《我的弟弟》,刊于1934年上海《金城》第一卷第四期;署名“宗廉译”的《我的弟弟》,刊于1935年上海新文学社编辑的《新文学》第二期;署名“汤泽恩译”(以目录所署的名字为准)的《我的小弟弟》,刊于1936年湖北省立蒲圻县民众教育馆编辑、发行的《民众先锋》第二卷第三期。
《新文学》杂志1935年第二期刊发的《我的弟弟》。
宗廉和汤泽恩的中译本,均说明译自巴金的世界语原著,但巴金的《我的弟弟》并未说明是译文。那么,这篇署名“巴金”的《我的弟弟》是否巴金自己翻译的中文本呢?
从“Mia Frateto”的“底稿”说起
巴金的第一篇世界语作品“En La Malluma Nokto”,在 他1993年3月13日复许善述的信中说是“随意写出来的,不曾有底稿”(刊于《巴金与世界语》)。巴金这里所说“底稿”,指作品的最初形态。那么,“Mia Frateto”有没有“底稿”呢?答案也在巴金的这封信中:
据“Mia Frateto”中译文,很容易找到这篇“散文”,就是刊于1931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的《我们》。短篇集《光明》(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确也收有《我们》。辜也平在《关于巴金〈Mia Frateto〉相关情况的补正》(《点滴》2015年第六期)一文中说自己“发现”了“Mia Frateto”的“原初形态”为小说《我们》,其实巴金早已说清楚。
据巴金信中所说,“Mia Frateto”并非直接由《我们》翻译成世界语的,而是由《我们》“改写”而成,且“有小的改动”。这通过比对“Mia Frateto”中译文与《我们》的文字可看出:文字自然有差异,但人物、情节和结构基本相同,“弟弟”的年龄由13岁改为11岁。
《我们》写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天后的9月29日深夜,是较早出现的一篇抗战小说,描写了一个13岁的孩子由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恐惧,恳求哥哥杀死他的故事。巴金作于同一时间的新诗《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流泪了》与《我们》刊于同期,则是一首较早的抗战诗,至今还有人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
此处顺便提及,汤的译文后有“本文以一二八战争为背景。译文有失真之处,由译者负责”的“注”,应有误。另外,小说《我们》初收于短篇小说集《光明》,后又收入烽火小丛书之一《控诉》(烽火社1937年版)。《光明》小说集现存《巴金全集》第九卷,《控诉》现存第十二卷,但两卷均全文收入了《我们》,“全集篇目索引”也重复列目,将来修订《巴金全集》时应予改正。
关于《金城》月刊
《金城》月刊,现有的大多期刊类工具书未著录,《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收录了该刊,并有如下介绍:
月刊。小八开本。1934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同年4月1日出至第一卷第四期后停刊,共出4期。刘家麒总编辑,文艺编辑沙蕾,联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该刊为综合性文艺杂志,旨在“贮集兴趣材料,调济人生的苦闷;用美术的印刷,有组织的编辑,供给大众一本酒余茶后自头至尾篇篇有兴味的刊物……要在1934年的出版界里,建筑条新的途径,本着光明的宗旨,灌输社会一种新的生活”(家麒《发刊》,第一卷第一期)。主要刊登小说、诗歌、漫画、体育消息、戏剧评论等,其撰稿人队伍可谓实力不俗,郭沫若、巴金、张资平、叶灵凤、林微音、王独清、徐仲年等人都有作品发表,女演员艾霞的诗作也曾见载于该刊……
《金城》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刊发《我的弟弟》。
刊有巴金《我的弟弟》的《金城》月刊第四期,是“天一影片公司特刊”,专事介绍天一影片公司的概况和发展动态,刊有全体演职员肖像、公司简介、出品列表和电影剧照等内容,并对“天一”即将公映的多部新片进行了介绍。
《金城》月刊在“天一影片公司特刊”出版以后即停刊了。关于停刊的原因,当时的报刊上有所报道。1934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发行的《出版消息》第三十四、三十五期合刊,在《文坛消息》栏目刊有一则“《金城》将停刊”的消息:“刘家麒与何嘉合编之《金城》月刊,近有将停刊消息,闻系内部意见不一之故。”何嘉是该刊的特约编辑,另有杜衡、黎锦明、赵景深和施蛰存等。其中,至少赵景深、施蛰存是巴金友人,他们相识于1932年朱雯和罗洪的婚礼上,巴金的《我的弟弟》应该是友人所约。
《我的弟弟》是巴金的译文吗
巴金有没有翻译“Mia Frateto”,其本人未曾提及,“李文”也未提出这个问题,巴金研究文献则无现成答案。“金文”刊布的 三 种“Mia Frateto”中 文 本,笔者在见到“金文”前已读过。当时的第一反应,刊于《金城》的《我的弟弟》就是巴金自己翻译的中译文。“金文”“初步推断”是巴金的中译本,笔者在这里简要地给出自己的分析,再试以确认。
比对巴金的《我的弟弟》与已见的“Mia Frateto”中译文,人物、情节和结构等完全相同,特别是“弟弟”的年龄是11岁,这也是笔者“第一反应”是译自“Mia Frateto”的理由,但仅凭这些仍不足以确定。因为从理论上说,也可能“改写”自《我们》,朱银宇在“金文”的“编者附注”中也提到这一点。
笔者以为,小说《我们》是较成熟的作品,没有理由去“改写”成“异题”的小说。若要“改写”,将“改写”自《我们》的“Mia Frateto”译成中文,应该更有价值。杨令德等的翻译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完全可确认,《我的弟弟》是巴金自己翻译“Mia Frateto”的中文本。
还有一个问题。巴金完成翻译的时间是文末署的“二三,四,二七”,即1934年4月27日。按此推算,这期《金城》最早也要在5月初出版,与以上介绍的该期于4月1日出版不合。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排除刊印错误外,也可解释,那就是这期的出版时间“脱期”了。具体原因是:集稿时间较晚,加上内部意见不一,“特刊”出版后将停刊,导致延时出版。同期刊有署名“子谦”的诗作《金钱和髑髅》,文后署“廿三,四,十一,于浦东”,即1934年4月11日作于浦东,就是佐证。
金给《金城》的稿件,为何选“Mia Frateto”的中译文?笔者的猜测是:1934年2月间,巴金从北京回到上海,刚创刊的《金城》向他约稿,巴金答应了写稿。笔者注意到,《金城》“发刊词”第一句“在这风雨飘摇国难紧张期内”,说的是当时国内反日抗日的形势,这也许是巴金决定翻译“Mia Frateto”的一个原因。3月到北京,为兑现“承诺”,巴金在百忙中于4月27日译完即寄回上海。
小说《我们》写于1931年9月,“Mia Frateto”发表于1933年7月,可能写于这年巴金南下旅行初期。半年多后的4月27日,又 将“Mia Frateto”译 成《我 的 弟弟》。由此看来,《我们》前后经过了从中文“改写”成世界语再“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又编入《光明》集和《控诉》集,说明巴金是十分“看重”这篇小说的。
巴金自己有没有翻译过“Mia Frateto”,终于有了确定的答案。特别地,巴金的中译文发表的时间虽然晚于杨令德的译文,但其意义与价值是不可比的,将来的《巴金全集》修订版就可以收入这篇巴金翻译的《我的弟弟》了。
到这里,巴金的世界语作品“Mia Frateto”,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已有杨令德、巴金、宗廉、汤泽恩和顾钟锦五种中译本。而“En La Malluma Nokto”虽也有五种中译本,但曾筠、小奇的中译文未曾见到,也因“二君译文原作字句多有未合”,巴金才自己决定重译的。
最 后,将“Mia Frateto”第 一句五个中文本的不同译文录于下,以作简单对照:
外面是大火,大炮和枪的声音,惊人的喊叫,号啕的痛哭和苦痛的呻吟。(杨令德)
外面是熊熊的火,大炮与来福枪的杂声,恐怖的狂呼,大哭以及痛苦的呻吟。(巴金)
外面是熊熊的火,炮声和枪声,恐怖的呼叫,哭喊以及痛苦的呻吟。(宗廉)
外面是大火,枪炮的声响,恐怖的叫喊,哀号和痛苦的呻吟。(汤恩泽)
外面是一片大火,枪炮的喧啸,骇人的喊叫,悲号和痛苦的呻吟。(顾钟锦)
中国第一家由媒体创办的读书类专业报纸
《文汇读书周报》
WENHUI BOOKREVIEWSINCE1985
《文汇读书周报》采编团队
张裕 zhangyu@whb.cn 舒也 xjz@whb.cn
蒋楚婷 jct@whb.cn 朱自奋 zzf@whb.cn
薛伟平 xuewp@whb.cn 金久超 jinjc@whb.cn
周怡倩 zyq@whb.cn
如果你喜欢本文,请推荐给他人或在【朋友圈】转发
点击标题下方【文汇读书周报】字样,关注我们的动态
文汇读书周报
或
whdszb
We HavetheDivineScholarlyZestBlessed
巴金简介是什么
巴金(1904~)现、当代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巴金资料
巴金简介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汉族。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人》为著名。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半真半假地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巴金爽快一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巴金《团圆》的内容简介?
《团圆》是巴金上个世纪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60年代初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后来长影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改名为《英雄儿女》。影片公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向我开炮!”影片中的英雄王成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
巴金的资料与作品简介
李尧棠(1904~2005),笔名巴金,字芾甘。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
巴金的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汉族。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人》为著名。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半真半假地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巴金爽快一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巴金简介资料
巴金代表作品:《家》、《寒夜》、《随想录》。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扩展资料:
巴金作品风格
就题材而论,巴金的长篇小说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并且带有强烈的自传性。他的短篇小说则题材多样,涉及范围相当之广。在巴金的作品中,家即社会,家庭是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
巴金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最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情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其中尤以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
同时高公馆的生活也是以作者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寒夜》通过描写汪家的解体过程揭露了当时大后方社会的黑暗。
作者着重表现的是小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比如婆媳争吵,夫妻失和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真实、细致的描绘表明,汪家悲剧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
这部作品又一次体现了巴金创作的特色,把家庭当作社会的缩影来描写以家庭生活画面来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除此之外巴金在《某夫妇》、《猪与鸡》、《团圆》等短篇小说中也有对这一题材的优秀运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巴金
周立民|巴金与傅雷的“君子之交”(下)
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翻译多了,傅雷想换换口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对他要译的梅里美的这两部小说,傅雷谈过看法,还保留了钱锺书对于别人译本的看法:“梅里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太巧,穿插的罗曼史也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此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锺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大约正是对于原有译本的不满意,傅雷才再译一个本子。《嘉尔曼附高龙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印数为一万册。傅雷翻译用的底本(或参考本)借自巴金,于是便有了傅雷这封还书帖:
弟怒庵拜启
二月二十七日
△1954年2月27日傅雷致巴金信
△傅译《嘉尔曼附高龙巴》封面及版权页
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从排版、校对到装帧设计,作者都享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问题到了我的‘行内’,自不免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傅雷说,他在装帧、版式乃至书的校对上的讲究,“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此言不虚。他有一封信中谈到工作状况:“这一年来从头至尾只零零星星有点儿休息,工作之忙之紧张,可说平生未有。……除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平明社,同在一城,相互来往的工作情况,没有留下太多文字材料,等傅雷的书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出时,因处两地,倒是留下不少工作信件。傅雷的“最严格”从这些文字中清晰可见,而且傅雷无形中将人文社与平明社对比起来,以平明社为标准要求人文社。将译本移到人文社出,一是平明社即将面临公私合营,行将不存;二是时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楼适夷是傅雷的老友,屡屡邀约。“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了,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三是傅雷没有直接说,人文社是国营社,平明是私人社,当时的文学出版正逐步纳入整体规划,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私营社给国营社让路责无旁贷,巴金和傅雷都不好多说什么。
移到人文社中,傅雷降低要求但是也力争自己的权利,关于校对,他致信出版社强调:
二、校样本人需看初校二校两遍(过去前后四校均由本人亲自,今在北京排,为节省时间起计,减为二遍),但有数点声明:
甲、本人每次校对,文字均有修改,虽然不多,但是一定有。因文章多看一次,必然多少会找出毛病来。
乙、版式的整齐美观,本人十余年来无时不加注意,故初二校样上常有统行情形批出,务请谅解。
在版式美观上,他始终坚持:
兹为服尔德《查第格》及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二稿事奉渎。自胜利以后,所有书稿前后校对,均亲自负责对底,因(一)对于出版格式,可随时批改,力求美观,合理;(二)对内容文字,多看一遍,即可多发现毛病,多修改一次。故一九五三年十月,适夷兄来沪商谈为将由平明转移人文,并约定以后专为人文翻译时,弟即提出均在上海发排,以便亲自照顾,免京沪间寄递校样,耽误时日。
至于弟坚持要各章节另起一面的理由,是因为古典名著不能与通俗文艺同样看待;《查第格》全书不到一八〇面,薄薄的本,很像小册子,不能单从节省纸张着眼。《于絮尔·弥罗埃》也要每章另起一面,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很复杂,有时还相当沉闷,每章另起一面可使读者精神上松动些。
总的来说,我处理任何事情,都顾到各个方面。校样从头至尾要亲自看,为的是求文字更少毛病,也为的是求书版形式更合理美观,要在上海排,为的是求手续简便,节省时间,也免除与排字房的隔膜。
他甚至为书名中的书法题词中,改用繁体字和简化字,而与出版社争辩:“在此全国上下提倡百花齐放之际,不知贵社能否考虑封面手写字体可由书写者自由,一方面为我国留此一朵‘花’,一方面也不必再在此时此刻立下清规戒律。”
傅雷的这种认真、细致,有时候未必得到出版社及时呼应,对此他只有焦急地一遍遍写信强调、呼吁,也有伤心地慨叹。“巴尔扎克各书移转人文后,先出精装本;但北京印刷条件甚差,公家办事亦欠周到,故样本寄到上海,本本皆有污迹,或装订,或印刷上的毛病。”“‘人文’新印的巴尔扎克精装本,已有三部寄来,可怜得很,印刷与装订都糟透,社内办事又外行,寄书只用一张牛皮纸,到上海,没有一本书脊不是上下端碰伤了的。封面格式也乱来,早替他们安排好了,他们都莫名其妙。插图铜板还是我在上海监督,做好了寄去的;否则更不像样了。”
傅雷对于精装本的质量有着自己的要求,“五四年十一月所印前五种巴尔扎克的精装本,成绩反不及平装本。”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毛病,确定标准,等于是手把手在教出版社怎么印书:“精装书外面加的彩色包皮纸,折进书里的一段纸往往太狭,拿在手里容易脱出,不久就破碎。原来是为了节约纸张,但到读者手里用了几天就破碎,岂不因小节约而造成大浪费?这也是我说的‘只打小算盘,忘了大算盘’的一例。光从降低成本着想而不替读者用的时间长短着想,就是我说的‘只顾眼前’的一例,而且是极端片面的。真要节约,就干脆取消那张彩色包皮纸!”从文字中,能够看出他的焦虑乃至恼火:
(二)即使是布面精装,如适夷兄译的《高尔基选集》:甲、封面凹凸不平;乙、胶水污点不少;丙、烫金有缺笔,或一字之内部分笔划发黑;丁、书角也有瘪皱情事。总结起来,仍是浪费。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作得好。
显而易见,限于条件,平明社的精装本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风却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对人文社的领导说:“将来倘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装本的话,希望注意一点: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这是有关原则性的问题,务盼赐予注意为幸。”他对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条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旧样式”:“封面装帧、题字、排印字体、书脊题字式样、各册颜色,希望全部维持原样,只改动出版社名称一项理由:倘没有充分理由肯定旧样式不美观,即无改头换面之必要;同时也可节约人力物力。”他甚至放出狠话,倘若达不到要求,宁可不印精装本,“希望郑重考虑承装工厂的技术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倘无适当技术水平的装订,宁可不印精装本,以求节约。”
傅雷的要求处处以平明社的书和做法为标准,由此返观,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满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的确,这套书的印装在今天看来也是难得的精品。四大卷,开本近乎方型,书封有外函套,封面简洁、经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还有给作者加印特装本的传统,让作者送人,也体现书的尊贵。黄裳、穆旦、萧珊的书,都见过这种特装本。傅雷在另外的信中称这算是开风气之举:“又《约翰·克利斯朵夫》,北京有指示要上海印精装本二千部,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经纸本的,算是替中国出版界开开风气。但成绩因条件限制,不能完全合乎理想。”我在1955年12月编印的《平明出版社图书目录》中看到:《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有四卷本的书籍纸精装本,定价是12.50元;另有上下两册的字典纸精装本,定价是16元。这种两卷本的字典纸精装本,我未见过,大概就是傅雷所说的“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经纸本的”。
△平明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53年9月版书籍纸精装本,该本印2900部,另有100部字典纸精装本
文人爱书,傅雷很珍惜这样的印本,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曾叮嘱:“新出的巴尔扎克,收到后来信提一笔——这是特印非卖本,勿随便借出去,搞丢了!”“特印非卖本”这并不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计划经济中,国营大社怎么会有这种例外,反倒是私营出版社有这种灵活性。还有一层不能忽视,巴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延续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译文丛书”的路子,编辑“文学译林”丛书,意在推出翻译精品,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他一直关注平明社的这套丛书。“西禾谈及巴金新组一书店(已与文化生活分家),想专出一套最讲究的文艺翻译,由西禾与他二人合编,说是决不马虎,迄今只收了杨绛一本译稿,听说好得很。此外又来问我要稿,也许新译的巴尔扎克会给他们。此外他们还想不出别人。不知悌芬有意半玩儿半工作的试试吗?但书店方面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你不妨与他谈谈,让他想想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些什么,可以来信商量。巴金的条件,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他是反对新办法的。”“《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阻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搞不出一些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这两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文学译林,由巴金和陈西禾合编;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杨绛译《小癞子》(1951年4月初版,印3000册)和傅雷译《贝姨》(1951年8月初版,印2500册),后来陆续增加的是傅译巴尔扎克诸书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傅雷特别强调巴金他们收稿之“严”“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严格、标准、眼光,巴金的出版社的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这也是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作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联系点。两个人的性格虽然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认真的人,都是切实做事的人,都是心怀理想的人。
傅雷还是一个热心人,他鼓励人译书,也为平明社这套丛书拉稿。1953年1月给巴金的这封信,就是介绍杨必译稿的:
杨必(1922—1968)是杨绛的妹妹,在她们家姐妹中行八,后曾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傅雷曾请她教过傅聪英文,很赏识她的才华,在傅雷和钱锺书夫妇的鼓励下,她开始涉足文学翻译,信中提到的《剥削世家》是一部小书,她后来还译过萨克雷的那部大书《名利场》,很受推重。虽说初涉译坛,杨必的“师傅”却非同一般:姐夫钱锺书、姐姐杨绛“代为校阅”,一代译宗傅雷“通篇浏览一过”,《剥削世家》译文质量大有保证,傅雷给出的判断是“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他甚至用红笔把排版格式都在原稿上批注出来了,如此推重和为其尽心,令人叹服。傅雷还向巴金提出一个要求:“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私营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书能力很低。这一点,傅雷在1951年给宋奇的信中谈到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篇幅太大,私人出版社资力和能力都有限,他暂时不转到平明社。我在平明社1952年9月初版、1953年2月再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页还看到一则声明,也谈到工厂繁忙,排印不及:“本书第二册原定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因排印工厂工作繁忙,致脱期甚久,劳读者悬望,甚为抱歉。第三第四两册决定于本年六月份同时印出,特此预告。”按照傅雷“一手包办”的说法,我怀疑这则声明出自他之手。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尽快的速度出书。《剥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册,也就是说在傅雷把稿子寄给巴金之后三个多月就印出了。该书在当年8月再版,增印3500册;1954年1月第三版,增印4500册,总印数达13000册,看来挺受欢迎。
杨绛在回忆杨必的文章中说:“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杨绛补充的信息是,《剥削世家》《名利场》都是钱锺书帮忙选定的书目并且确定了书名。傅雷在给宋奇的信中补充的信息是,这书初译稿,钱锺书不满意,杨必重译了一稿:
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售罄,迄未再版。最近杨必译的一本MariaEdgeworth;Castle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我已和巴金谈妥,此书初版时将《小癞子》重印。届时必当寄奉。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励你译书,即为此丛书。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
△杨必译《剥削世家》
杨绛的《小癞子》初版印3000册,两年后已经一册难求了。在傅雷的建议下,平明社重新排版重印,于1953年10月出了重排一版,印4000册;1954年5月又印重排第二版,增印2000册。傅雷对杨氏姐妹的译笔很是推崇,也曾感叹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杨氏姐妹那么灵活:“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傅雷曾对杨绛说过“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看来他是真心喜欢杨氏姐妹的译文。
杨必之外,傅雷还动员宋奇(宋琪)译书:
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要顾到这点,恐怕Jane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这两天约他谈,还想当面与巴金一谈。因西禾此人不能负什么责任。
傅雷屡次提到“文学译林”丛书,乃是他极为欣赏巴金办出版社这种“不问读者”的原则,其实是为了文学、出版、文化的积累不计名利的气魄。朋友有各式各样,有的朋友,可能不在于世俗生活中来往多少,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认为傅雷和巴金的友情就属于这一类。
遗憾的是,平明出版社只在出版史上存留了短短的五六年,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提到了它的结束,虽未置一词,但我隐约能读出几分惋惜:“平明出版社年底归并公家,与‘新文艺’合。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嘉尔曼》则移交‘人文’,楼伯伯来信,说钱伯母,必姨的两本小书也要向平明讨过去。”
俱往矣,距离此信六十年后的2014年,在傅雷夫妇忌日(9月3日)的前一夜,外面下着大雨,我在武康路巴金故居中整理资料,突然发现一个印着黑字的信封,打开看,里面是“举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仪式通告”,里面,还夹了一张代办花圈的通知。通告的内容简单,又冰冷: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几十年过去,这张冰冷又沉重的通知在那一刻出现,仿佛是天意?在我的书房中,有一尊青年雕塑家高旷寓送给我的傅雷雕像,傅雷围着围巾,手执一卷书,身材颀长,飘逸,我想到人们对他的评价“孤傲如云间鹤”。我也想起1987年巴金写给苏叔阳的一封信,是回答苏叔阳关于老舍之死提问的,由老舍,巴金谈到傅雷:
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巴金把他们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钦佩他们“有骨气”,表示他们是不能被遗忘的“炎黄子孙”。是啊,“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毕竟是知识分子,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传统。
(本文注释已略去)
作者单位:上海巴金故居 辽宁省作家协会
巴金的资料与作品简介
1904~2005),笔名巴金,字芾甘。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
巴金的简介
巴金生平: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